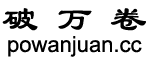汉末太平道 第19节
“道奴,你说的不错。就如实告诉师父!再找他老人家要一本符书来…”
“嗯!…哦,对了!我这同乡临走的时候,还对我说。说我天生巨力,棍棒也练的娴熟,但离那些真正厉害的惊世人物,还是差了一层…他说,若是我以后有了时间回乡,可以去涿郡寻他。他知道有个武艺厉害的侠士,就在涿郡乡里!…”
“涿郡乡里,武艺厉害的侠士?”
张承负怔了怔。常言道“穷文富武”,要找个真正厉害的武艺名家,可是难得紧。那些名声在外的名家,若是没有豪族的身份,几乎是无法拜师的。他们更不可能收黄巾门徒,因为太平道本身,就相当于一个师门了。有师父你还来拜什么?
“这位侠士,名叫什么?”
“叫关君。据说是个二十出头,刚刚弱冠的青年,也不知是从哪学的一身惊人本事。他好像是并州还是河东人,不知犯了什么事,避难来到涿郡不久。平日里,他就隐居在乡里,行事很有些侠气。他武艺极高,刀矛皆精熟,寻常三五人一起上,都不是他的对手!…”
高道奴看向北边,有些向往的说道。
“好像那位大豪刘君,也对这个关君颇为称赞,亲自上门拜访了一次。还请这位关君,指点他手下的一个张姓少年。那少年和你年纪差不多大,也都天生巨力,只是武艺上差上一筹。据说只要有名家指点一二,就能脱胎换骨…”
“并州或者河东来的侠士关君,武艺极高,刚到涿郡不久?!”
张承负神色微变,心中波涛汹涌。他沉吟不语,明确了猜想。若是说,这天下的英雄豪杰,有几人有可能与他同道…那恐怕这位底层出身的关君,就是其中之一了!
至于另一位大豪刘君,还有刘君手下的张姓少年,虽然同样与百姓亲善,却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路。未来必然无法成为同道,只能拔剑相向。
“关君…关君.刚到涿县的关君!”
张承负垂下眼睛,想了又想,突然放下了手中铁锹。他拉着高道奴,大步就往住的屋子走。
“道奴,你过来,帮我再办件事!”
“啊?”
“我得写一封信,给这位涿郡隐居的侠士。然后,你骑上马,帮我送给你那位涿郡同乡,请他带给关君!”
“啥?我这才刚回来,你就让我再跑一趟?”
“没办法,我一不认识人,二不会骑马,三不是他涿郡乡党,如何能请托?就只有靠你了!”
说着,张承负已经到了屋中,取出了纸笔。他闭目思索了许久,在脑海中勾勒着那个人的形象与性情。许久之后,他才深吸口气,落笔写到。
“太平道张承负顿首拜言:足下见世道不公,挺身刺吏,替天行义,此诚古之大侠也。昔人有言,父母之仇,不与共天;士之所许,一诺千金。
承负闻君义烈非常,胸怀炽炽,感而动心。有一生死之重事,愿以性命相托,求君一臂之助!明年之际,必亲诣拜面,陈其始末。今以我太平道所藏经卷为信,愿君执此,知我志不诬也…”
第24章 不劳动者不得食,就连豹猫也一样
庄里农民的土屋只有一丈高(2.31米),装饰简单朴素。四壁是土坯砌筑的泥墙,顶上覆盖着厚厚的茅草,还有引导雨水流下的瓦片。那种正经的窗户是没有的,只有一面直棂窗,一扇木门,能够透进些光来。
而屋内的陈设,也就是一个坐着的草席、一个睡觉的草塌、一个矮小的案几、一个储物的木箱,再加一个储水的陶罐。这就是全部的家当了。
此刻,张承负就跪坐在草席上,提笔在案几上写完了信。随后,他把写信的黄纸折好,用一块带槽的小木片盖住,再用缄即捆绳系紧,绳结处加盖上一团黏土封泥,按了个手印。这就是“封缄”了,防止别人提前打开去看。嗯,这种密封,防君子不防小人。
“啊?这封信,还要封缄吗?”
高道奴有些不解。他看了看神情认真的张承负,迟疑道。
“我的那位同乡,应该是可靠的,无需这么提防…”
“不是防他,而是防那位刘君。”
张承负笑了笑,没多解释。接着,他又取出一个木匣函盒,把封缄的信放在下面,伸出手道。
“没卖出去的那册符书呢?给我。”
“你要做什么?”
“送关君。”
“什么,送人?!这可是一百斛粮食,加十头牛和牛车!”
“不。这符书值不了那么多,那是我太平道的面子值钱。把符书给我。”
“…那也是五十贯…”
高道奴悻悻的念叨了两句,还是拿出了那本没卖的《太平经》。张承负接过符书,想了想,又从箱中取出两页自己写的《太平新经》,夹在了最前面。然后,他把这册书一卷,放到木匣中。最后在木匣的盖子上,他又上了一道封泥。
“这么小心…这位关君很重要吗?”
“很重要。若是能得他相助,我就可以报仇了。而把他请过来,也可以教你武艺。当然,更重要的是这个人。他是位真正信义的侠士,可以托付性命。”
张承负笑着说了两句,把木匣递给高道奴,叮嘱道。
“把这个木匣送给你那同乡,让他转呈给关君。就说是你请求指点武艺的信。赶紧骑马去吧!快去快回!”
“行!”
高道奴点点头,把木匣往怀里一揣,大步踏出门。很快,门外就响起马的嘶鸣,拉长着远去了。而张承负有些羡慕的,看着高道奴骑马的背影,自语道。
“马作飞快,三倍于奔跑。在这汉末的大时代,不会骑马怎么能行呢?骑马得学啊!…”
“等道奴回来,让他教教我。至于现在,还是继续挖土吧!…”
马作的卢飞快,铁锹挥舞不停。高道奴去了三日,回来时依旧英姿飒爽,满面红光,嘴上还沾着油。而张承负挖了三天土,干出了小十方土,满头满脸都是土。两人一见面,互相瞅了瞅,都有些想笑。
“送到了?”
“送到了!”
“又吃肉喝酒了?”
“嗯,肉好吃,酒也好喝!”
“既然吃饱了,就下来一起挖塘!玄力,把你的铁锹,给你高师,你换一把木头的。对!他挖土厉害!”
“啊?”
张玄力哼哧哼哧的跑过来,把一把铁锹塞到“高师”手里。然后,他又跳下陂塘,哼哧哼哧的挖起土来。而高道奴握着铁锹,单手摸了摸下巴,吐槽道。
“在我同乡那里,他一口一个青年才俊、少年英雄,又是请我喝酒,又是请我吃肉…而等我回来,你却只会招呼我挖土?也不让我歇息两日。”
“那究竟是喝酒吃肉好,还是挖土修陂塘好?”
“能不能两个都选?”
“暂时还不行。只能选一个。”
“算了,那还是挖土修陂塘吧!毕竟,喝酒吃肉虽然快活…但只有修陂塘,才是在救人!”
高道奴叹了口气,从河坎上跳下,与张承负并着肩。接着,两人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,熟练的挖起土来,就像两个大号的土拨鼠。他一边挖,一边嘴里还不闲着。
“你说,那个关君,是个能和我们一起挖土的吗?”
“嗯。有可能。”
“那其他名声在外的豪杰呢?”
“那就很少很少了。那些士族和豪强,绝大多数都不可能,弯下他们的腰,跳到这土坑里干活的。”
“哎!看你选的这道!罢了,就和你一起干吧…”
高道奴摇了摇头,专心致志的挖起土来。劳动的口号在田野上响起,数以百计的丁壮孩童,都在努力的忙碌。同道的豪杰很少很少,可同道的百姓,却很多很多~~
八月在农忙与干活中过去,流着汗水,飘着谷香。九月肃霜,深秋带来了寒意,也到了准备冬衣的时候。而庄子里的妇女们,都从塘上下来,为童子们缝制起冬衣来:外面两层麻布,里面塞上满满的稻草、芦苇、麻絮。这就是农民们简单的冬衣了。
至于世家大族们,则会穿狐裘、貂裘各种毛皮衣物。而更常见的则是丝绵衣,用蚕丝棉填充帛布。像是马王堆中出产的丝棉衣,能达到3厘米厚,单是一件衣服所用的蚕丝与布帛,就价值万钱。
“悲哉,秋之为气也!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。”
“教人悲伤啊,秋天的气氛。大地萧瑟啊,草木衰黄凋零。”
在发黄的原野上,张承负哼唱着悲伤的《九辩》,身体一动不动。他努力骑在一匹黄马的背上,驾驭着马慢慢踱着步子。而旁边的高道奴单手拉着缰绳,直接躺在了红马的背上,看着非常辽阔和深邃的秋天。
“承负,你再不骑快点,我就要睡着了。”
“.那你睡吧!不能再快了,再快我就要掉下去了。这没有马镫,马跑起来的时候,你是怎么坐稳的?”
“马镫是什么?你是说一边垂下的、方便上马的绳套吗?…”
高道奴挠了挠头,仅仅凭着腰力,自然的从躺着变成了坐着。他看着张承负别扭的劲,笑着道。
“你不要和马的力气对着干!怎么坐稳?合着马的拍子,就自然而然的稳了啊。你由着它的劲,上上下下,整个人松弛下来…看你这样使劲控着马,不知道有多累人!…”
“松下来?由着它的劲?”
张承负慢慢的浑身放松下来,而感受到背上烦人的家伙,终于松了控制它的巨力…胯下的黄马立刻马蹄飞跃,然后用力一甩!马背上的张承负,顿时消失不见…
“呃?!…这家伙?!呸呸呸!”
张承负满脸是泥,从地上爬了起来。好在没有马镫,也不用担心被卡住,然后被马拖着走。他看着“一骑绝尘”的黄马,手指捏的咯咯响。而旁边的高道奴笑成了个摇晃的葫芦,胯下的红马也跟着一跑一晃。
“哈哈哈,笑死我了!马是最有灵性和聪明的!你这马估计在心里,早就烦透你了!你得好好帮它刷身子,喂它好吃的鲜草和干豆,才能让它信任亲近你…”
“驾!驾!我先去帮你把马牵回来!”
“行吧!那我继续挖土去了!”
张承负拍了拍泥土,向河坎飞奔而去。每天半个时辰的骑马练习,就到此结束。而他现在骑马的速度,还不如腿着跑呢。至少他跑起来两脚着地,能使上自己惊人的力气,跑的比谁都快!
日升月落,河边的陂塘就像沙滩上的沙雕,被无数双忙碌的手与汗水,逐渐塑出了模样。百亩的塘底已经挖完了大半,同样开始夯筑起来。至少要夯实三层,弄出一尺以上的实心夯土层,才能保证储存的水不会渗漏。
“砰!砰!砰!”
“嘿!哟!嘿!哟!”
木槌连天震响,就像在大地上敲击出的鼓点。而众人有节奏的口号,好似九州最古老的祭歌。这种集体协作的劳作,最是塑造人的精神。陂塘上无论是丁壮还是童子,都有了晒黑的脸庞,带着一种坚韧的神态。
就这样忙到了九月底,夏播种下的大豆小豆,也终于陆续成熟了。豆子的生长期明显比粟米要短,三个多月就够了。田地中到处飘着豆子的味道,带着点香,带着点甜。这种收获的味道,很快就引来了灰色的斑鸠,引来了灰黑的田鼠,更引来了捕捉飞鸟与田鼠的豹猫。
“嗷呜!…”
豹猫的叫声颇为低沉,就像豹子一样。张承负抱着收获的豆子,听到声音望去,就看到一只足足一臂长的豹猫,竖着半臂长的尾巴,叼着一只田鼠,蹲伏在豆仓的周围。它浑身布满黑色斑点或玫瑰状斑纹,面部有白色眼线,耳背黑色,活脱脱一只小号的豹子,充满了野性的味道。
“貍,伏兽也,似貉而小…这种豹猫能够驱鼠,可是粮仓周围的益兽。看它瘦成这样,确实是饿极了。旱灾的年份,连豹猫都吃不饱…”
张承负放下豆子,笑着对周围的童子讲了几句。随后,他心痒难耐,轻步向前,对这豹猫唤道。
“好猫儿!不要动…等我靠近过来,摸一摸你…”
少年温和的话语未落,两脚猛地一蹬,身影忽的一个飞扑。他速度极快,出手又迅捷又凌厉!然后,他扑了个空,手中只抓了一簇猫毛。
“嗷!呜!…”
豹猫吃痛的叫了两声,如电一般跳上粮仓的顶端,炸毛的盯着下面的少年,差点连嘴里的田鼠都丢了。张承负看了看手中的猫毛,尴尬的笑了笑,又对周围的童子道。
“毛,眉发之属及兽毛也!可以制笔,也可以御寒。嗯,若是能养上产毛的羊群,剃毛纺织成衣,或者填充在冬衣里…冬天就没有那么寒冷了!…”
张承负笑着、说着,背起双手,又一次藏起这具身体中的少年心性。他老神在在,讲起说文解字,也在泥地上书写起来。而今天要讲的、最重要的一个词,就是“丰穰”。
“丰,苞也。象草木丰盛之形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