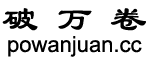最红楼 第102节
尤三姐冷笑道:“二姐什么意思当我不知?这是瞧见远哥哥要发迹了,便舍了面皮也要贴上来,你早干什么去了?”
尤老安人就道:“你看看,自家姊妹,你闹个什么劲儿?再说,我看这事儿也是好事儿。”迎着尤三姐不解的目光,尤老安人道:“哪儿有妹妹嫁了去,姐姐还待字闺中的道理?”
这十根指头还有长有短,尤老安人心下自然又有偏心。尤二姐素来柔顺,她说什么就是什么;尤三姐却不同,起先就不以为然,近来更是说一句顶三句。
尤老安人的确瞧错了陈斯远,这人不说举业如何,能得燕平王赏识,来日就有一番富贵。这三姐儿若是嫁了去,只怕来日不好打秋风……倒是二姐儿嫁了去更好。
至于尤三姐心下不满……大不了一道儿嫁了去就是了,如此还省了一份嫁妆呢。
到时候姊妹同心,那林家姑娘再如何高贵又如何斗得过?
尤老安人便要与尤三姐讲道理,尤三姐又哪里肯听?当下竟扭身便走。
尤老安人也不在意,低声与尤二姐道:“莫管她,气个一两日也就是了。”
尤二姐垂着螓首应下,想起方才倒在陈斯远怀中,那人的手可没闲着,这会子便觉胸口有些别扭……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却说陈斯远一路回返荣国府,此时尚不到申时。
方才交还了马匹,便有门子余四寻来,说是大太太有请。陈斯远往东跨院去了一趟,邢夫人便雀跃着絮絮叨叨了好半晌。
说的自是海贸之事,这几日传扬出去,果然有不少女眷寻来,或是代自家插一脚,或是干脆自个儿拿了体己,汇总在一处竟也有两万两出头!
邢夫人算算,过半年平白就能赚两千两银子,如何不高兴?
此时不但王善保家的在,连一直不曾露面的陪房费婆子也来了。扫听了才知,原来费婆子先前染了病,养到年前方才好转。
有外人在,陈斯远自是不好与邢夫人说些悄悄话,于是过得半晌便起身告辞。
邢夫人自然也极为扫兴,瞥了王善保家的与费婆子,思量着王善保家的好打发,这费婆子又如何打发?说不得来日须得费心给这二人寻了差事,免得整日介守在自个儿身边,再不好与那小贼往来。
陈斯远重进荣国府,迎面便瞧见两个婆子夹着一哭喊的丫鬟行了出来,那丫鬟随身只一个小包袱。
眼瞅着俩婆子将那丫鬟丢出角门,陈斯远叫了余六过来,低声问道:“这是怎么了?”
余六道:“瞧着是宝二爷房里的碧痕……这是犯了事儿了?”
碧痕?陈斯远心下莫名,一时间倒是没想起这丫鬟何时被撵出府的了。转念又觉可惜,若这回撵的是晴雯就好了,说不得自个儿还能捡漏呢。
想起早间时要往省亲别墅游逛的心思,陈斯远干脆绕过东院儿,自角门进来,过穿堂到得三间小抱夏前,一旁就是李纨房,挨着凤姐儿院儿有一条夹道。
行不多远,一旁有水房,挨着水房便是一处角门。陈斯远径直入得内中,抬眼扫量过去,便见甬道齐整,山石林立,各处亭台楼阁修了大半,怕是再有一月光景便能齐备。
陈斯远心下啧啧有声,冬日里赶工,这里外里要多花费出去多少银钱?
转过翠嶂,陈斯远往西行去,过了几座桥,瞧着四下建筑,依稀能分辨出潇湘馆、缀锦楼、秋爽斋等,又往北行去,沿曲折游廊而行,眼前便是一处石洞。
正要往里行去,忽而听得内中有女子哀求、男子喘息之声。
陈斯远顿时停步顿足,四下扫量一眼,抄起根遗落的木料防身,只当是施工的仆役起了歹心,将谁家的丫鬟劫持到了石洞里。
陈斯远大喝一声:“谁?”
内中男声为之一噎,继而有女声嚷道:“救,救命——”
陈斯远提了木料开道,挪步往石洞寻去,忽而便见内中一小厮服色之人慌乱裹着衣裳,见了陈斯远竟扭头就要跑。
那人瞧身形比陈斯远还单弱,陈斯远顿时凭空生了胆气,发喊一声,一棒子砸在其肩头,那人怪叫一声,也顾不得拾掇衣裳,竟踉跄奔行而去。
陈斯远追了两步,又听身后求救之声,这才扭身回来观量。石洞里昏暗,陈斯远仔细观量半晌,忽觉这女子面善。想了半晌方才试探道:“司棋姑娘?”
那司棋罗衫半解,也不知中了什么药,这会子只梦呓道:“热,好热啊……”
司棋说道:“一个女人配一个男人。我一时失脚上了他的当,我就是他的人了,决不肯再失身给别人的。我恨他为什么这样胆小,一身作事一身当,为什么要逃。就是他一辈子不来了,我也一辈子不嫁人的。”
‘一时失脚’,明显潘又安诱骗了司棋。此女毁誉参半,从不同角度分析会得出不同结果。
说她不忠心也对,毕竟坑了迎春不说,还要将迎春拖下水;说她追求自个儿幸福也没错,毕竟迎春不被重视,姻缘堪忧。
私以为,司棋烈有余、忠不足。
第128章 效红拂故事
蟹壳青底子刺绣镶领黛绿缎面比甲已然扯开,内里是月白圆领夹棉袄子,下身霜色长裙提起大半,露出内中的裤腿来。一截白生生的小腿来回踢腾,眸子愈发迷离,一手扯着自个儿衣裳,一手探过来便将陈斯远胸襟扯住。
陈斯远犯了难,这会子若是将其抱了出去……好说不好听啊。且出了这等事儿,不拘犯错的是不是司棋,难免事后被赶出府去。陈斯远这人底线灵活,却没想过要害无关人等。
定睛瞧了个仔细,便见云鬓散乱,发丝遮了一张鹅蛋脸,眉眼细长,面相偏冷。身子高大丰壮,估摸着比陈斯远还要高半头,偏此时媚态十足,真个儿是‘乌云叠髩、粉黛盈腮,意态幽花秀丽,肌肤嫩玉生香’。
陈斯远如今虽不缺女子,奈何方才被尤二姐撩拨得心下火热,此时虽隐隐意动,却好歹按捺了下来。
这会子还是正月,在石洞里厮混一场,说不得就染了风寒。且外头人来人往,万一被人撞破行迹,那可真就说不清了。
他当下起身便要去叫了婆子来,奈何身子刚起,便被一股子巨力扯得重新俯身下来。
陈斯远一阵无语,再用力……又被扯得踉跄了下。
心下不由得暗忖,无愧高大丰壮,这力气放在前世岂不成了金刚芭比?
这会子司棋已然纠缠过来,嚷着‘热’,檀口一张一翕,朝着陈斯远面上胡乱啄来。
陈斯远暗忖,这怕是中了媚药啊。
当下略略思量,眼见一双丰润双腿绞个不停,陈斯远便任凭司棋胡乱啄来,一只手探下去,谁知司棋顿时呻吟出声。
陈斯远苦笑道:“说好了,我如今可是救你,你可别害我。”
当下再无二话,只依着司棋喘息施为起来。
也不知过了多久,司棋只觉又缥上云端,又从九天之外坠落下来,紧随而来的是好一阵茫然无措。
鼻息弹回来,温热扑在面颊上,她迷蒙着眸子看过去,便见陈斯远已然退在一旁,蹲踞着观量自个儿。
司棋别过头去,只觉羞得要死!
须臾,就听陈斯远道:“咦?可是好了?”
司棋抽泣两声,胡乱抹了面上泪花,窸窸窣窣拾掇了衣裳,起身跪地朝着陈斯远连连磕头。
“诶?你这是做什么?”
司棋哭道:“亏得远大爷相救,不然,不然我——”
陈斯远叹息道:“方才那人……你可识得?”
司棋犹豫着点了点头,却没说出话来。那人便是其表弟潘又安,生得品貌风流,又惯会说花言巧语。
司棋为迎春大丫鬟,这几年与潘又安往来不多。虽隐隐察觉潘又安有爱慕之意,却也守着本分规矩。今儿个潘又安又寻人递了话儿来,说是得了一些茯苓霜要请司棋来吃。
司棋便来这未建成的园子里等候,二人相见,果然便见潘又安拿了个小巧瓷碗,内中是牛乳拌好的茯苓霜。
二人到得石洞中享用,谁知司棋方才吃了半碗便觉头晕目眩,旋即便不受自制地浑身发热。
再往后眼见潘又安宽衣解带,司棋哪里不知其存着什么心思?
司棋极力叫嚷,偏声音有气无力。当时只觉心下凄凉,日后怕是要委身表弟潘又安了。偏此时一声怒吼,杀出来个远大爷,将那潘又安打跑。
再往后……司棋不敢再想,只想寻个地缝钻进去。
陈斯远见其只是点头,并未说出那人姓名,便也懒得多事,起身道:“你也没事儿了,那就早些回去吧。来日若是需要我作证,只管来寻我就是。”
司棋心下一横,抬起螓首道:“那人是潘又安,是,是我表弟。”
陈斯远道:“你想怎么办?”
司棋咬着下唇有心发狠,一时间又狠不下心来,陈斯远见状就道:“那等你想好了再说?”
司棋这才点了点头,又可怜巴巴看向陈斯远。
陈斯远道:“罢了,那我先回了……这事儿闹的。”
陈斯远再不停留,绕过盘山道,自后园门出来,正对着便是自家小院儿。红玉、香菱、柳五儿与芸香一道儿迎了出来,赶上年节,府中丫鬟也难得放松起来,时而便聚在一处耍叶子戏。
芸香眼尖,招呼一声忽而惊疑道:“咦?大爷的衣裳怎地湿了一大块?”
陈斯远低头观量,见下襟果然湿了一大块……是了,好似是第二回司棋弄的?
这事儿不好张扬,陈斯远便道:“别提了,也不知哪个顽童用鞭炮炸积雪,生生溅了我一身。”
积雪?红玉暗忖,这会子都开化了,哪里还有积雪?
进得内中,陈斯远净手更衣,干脆换了一身衣裳。红玉勤快,用木盆装了衣裳便要送去浆洗。待出得小院儿,红玉隐约觉得气味不大对,低头凑近湿润处嗅了嗅,顿时面上古怪起来。
她又不是没经过人事儿的,哪里嗅不出内中古怪?当下只当是苗儿、条儿那两个小蹄子又勾搭自家大爷了。旋即又埋怨起来,自家大爷自打年三十恣意了一回,如今总寻机扯了香菱与自个儿胡闹。
大爷才多大年岁,铁打的身子骨也撑不住啊,偏生他自个儿还不自知。红玉拿定心思,回头儿总要与香菱计较一番,合该好生劝劝大爷才是。
东跨院。
司棋冷着脸儿进得厢房里,绣橘见其发髻散乱,背后衣裳也脏了,便问道:“姐姐这是怎么了?”
司棋只道:“摔了一跤。”
二姑娘迎春正与探春手谈,闻声扫量一眼,虽略略蹙眉却也不曾放声。探春正思忖着棋局,待好不容易落下一子,抬眼再看,那司棋已去里间换了衣裳。
司棋枯坐炕头,想着今日种种,既心酸又庆幸。
心酸的是,表弟潘又安竟是这等狼心狗肺的,竟拿了药要夺了自个儿身子!庆幸的是,亏得那位远大爷撞破,还……还替自个儿解了药力。
司棋起先还是愤恨,恨不得这会子就去寻了那潘又安,将其暴打一通。可过得须臾,眼前便只剩下陈斯远那怜惜的眼神儿。
司棋逐渐痴将起来,右手下探抚在衣襟处,心下古怪得紧——原来还有这等古怪法子,也不知那远大爷是如何学了去的。
正思量间,外间有人叩门,道:“二姑娘可在?我来寻司棋说说话儿。”
绣橘去开了门,却是潘大年家的来了。
司棋搭眼一瞥,便见潘大年家的神色慌乱,与司棋对视一眼顿时讪笑招手:“快来,婶子寻你说说话儿。”
司棋又气恼起来,将脏衣裳一丢,起身迈步出来,与潘大年家的一道儿出了厢房。这内院不是说话的地方,潘大年家的便引着司棋到了三层仪门外的那处僻静厢房里。
潘大年家的关了房门,四下观量着见无人走动,回身紧忙作揖道:“司棋,我替安儿给你道恼了,他也是心下倾慕你——”
“住口!”司棋恼道:“倾慕我就是这般倾慕的?茯苓霜里头下了迷药,呸!好个倾慕!”
“这,他也是错信了茗烟的鬼话,这才寻马道婆买了迷药。”
司棋哪里肯信?只冷哼一声避过头去。
潘大年家的上前来低声道:“千错万错都是安儿的错,要不你说该如何处置?”
司棋正是气恼的时候,横了婶子一眼,道:“处置?也不用处置了,远大爷可是认出了他,这会子已跟二奶奶说了,他往后就等着去庄子上吧!”
荣国府处置家奴不过几个法子,罚月例,打板子,打发到庄子上去,撵出府去,最严重的干脆打死了账。
上一篇:大明:伴读万历,我爹张居正!
下一篇:返回列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