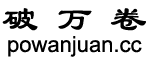最红楼 第416节
妙玉立时恼了,道:“既寻不回来,官差还有脸要茶水银子?”
清梵道:“韩嬷嬷说请神容易送神难……若不给些茶水银子,只怕官差便要生事呢。”
妙玉好一阵无语,只得打发清梵往前头送了二十两银子去。
清梵才走,便有智能儿来寻。
待进得内中,便与妙玉道:“姑……住持,庵中米粮已不够三日之用,师姐们让我来问问住持如何采买。”顿了顿,又道:“另则,侧殿烧了一半,只怕修葺起来也要银子。”
妙玉道:“米粮之事,只管去寻清梵。至于侧殿……且留着吧。”
她心下想着,左右地契不在自个儿手中,这修葺自然不会落在自个儿头上。
答对了智能儿,还不等妙玉静下心来,前头又出了事儿。吵嚷喧闹之声,便是在跨院里也听得真切。
少一时便有清梵哭丧着脸儿来寻,道:“姑娘,不好啦!有个卢员外拿了地契领着家丁寻来,说此地已为其所有,要咱们三日之内尽数搬离。另则,侧殿烧了大半,那卢员外还要咱们赔付银钱呢。”
妙玉气得浑身哆嗦,起身铁青着脸儿道:“那侧殿又不是我烧的,凭什么要我赔?”
清梵咬着下唇不言语,只瞧着妙玉。那意思是,众女尼都没银钱,还称妙玉为住持,可不就要妙玉来赔?
妙玉又不是傻的,心思一转便明白过来。当下叹息一声儿,再也扮不得高人,只好与清梵往前头寻去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却说这日陈斯远品评过众金钗诗词,虽逐个都赞了,心下却也分了高下。黛玉才情卓著,自是头一等的。让陈斯远惊奇的是,那薛小妹才情不让宝姐姐,二者竟难分伯仲。
惊奇之余,便有芸香送了帖子。
陈斯远过问一嘴,芸香只道有仆役打后门儿送来的。陈斯远铺展开扫量一眼,立时收拢了——此番却是薛姨妈来信相邀。
算算二人好些时日不曾亲近,陈斯远自是心猿意马。当下读书半日,晌午时推说与友人宴饮,偷偷摸摸便去了大格子巷。
那薛姨妈早就来了,二人小别重逢,自是好一番缱绻缠绵。待亲热过后,薛姨妈便说起正事儿道:“你得空往梅翰林家中去一趟,万万不可让琴丫头的婚事成了!”
陈斯远问道:“这是怎么个说法儿?”
薛姨妈翻了个白眼道:“你又何必明知故问?有了梅翰林做靠山,那皇商的差事岂不是要落到二房头上?”
所以女子有了权势最容易小性儿,薛姨妈此举颇有‘宁与友邦、不予家奴’的意思。
陈斯远便笑着道:“我与梅冲谙熟,先前此人几次三番推拒婚事……错非梅翰林含糊其辞,只怕这婚事早就作罢了。”顿了顿,又问道:“那二房的银钱……”
薛姨妈道:“我只说留在账面上,等年底归拢了再算给他!”
薛姨妈没说到底多少银子,可瞧着其肉疼的模样,想来最起码也要二、三万银子。陈斯远好生安抚一通,薛姨妈记挂薛蟠又闹事,急急忙忙便回了老宅。
陈斯远眼看天色不早,施施然回转荣国府,谁知甫一进得清堂茅舍,便见篆儿瘪了嘴正与红玉说道着什么。
见了陈斯远,那篆儿立时得了主心骨,上前道:“远大爷,你这回可得帮我们姑娘一遭。”
陈斯远讶然道:“表姐出了何事?”
篆儿几次欲言又止,说道:“还请远大爷移步。”
当下二人进了内中,篆儿这才说将起来。却是下晌时清梵又登门央求,只道妙玉并无银钱傍身,求邢岫烟帮衬。
邢岫烟推却不过,便将手头的银钱凑了凑,送了那清梵五十两银子。
陈斯远听得云山雾罩,暗忖那妙玉就算断尾求生,手头总有个两万左右的财货,这才几日便又来求邢岫烟?
正纳罕间,外间红玉道:“表姑娘来了。”
陈斯远紧忙起身来迎,便见邢岫烟蹙眉入内,显是朝陈斯远略略点头,随即瞧着篆儿道:“多嘴!谁让你来的?”
第303章 风摧兰蕙
篆儿闻言瘪了嘴道:“姐姐啊,再是好心也没这般好心的,那银子都给了她,姐姐与我不过了?”
邢岫烟如今还住在缀锦楼,用的都是二姑娘迎春的丫鬟、婆子,虽因着陈斯远之故,那些下人不好再给邢岫烟脸色,可总不好平白使唤人家,隔三差五总要给些赏钱才是。
邢岫烟被陈斯远扯着落座,气恼道:“我有月例银子在呢。”
陈斯远纳罕道:“舅舅、舅母不用表姐接济了?”
邢岫烟说道:“今儿个姑妈发了话儿,往后让我爹妈往她庄子上常住去,说庄子里不用什么用度,再不用我分出银子来给他们。”
陈斯远愈发纳罕,赶忙追问缘由。
却是近来王夫人与凤姐儿斗得愈发厉害,王夫人的陪房与投靠了凤姐儿的贾家家奴彼此寻了马脚,时常便要闹到管家赖大跟前儿。
因着赖尚荣一事,赖大早没了脸面,私底下又得了贾母吩咐,自是唯凤姐儿之命是从。这般拉偏架,王夫人一系下人很是吃了亏。
许是狗急跳墙,便有下人攀咬出邢忠贪渎之事。凤姐儿好不容易与邢夫人缓和了,自是不想再闹得生分了。于是昨儿个夜里往东跨院去了一趟,二人如何说的暂且不知,只知今儿个一早邢夫人寻了邢忠夫妇发了好一通邪火,到底将二人打发去了自个儿陪嫁庄子。
邢岫烟不知缘由,陈斯远却大抵能忖度出几分。那邢夫人可一直不曾熄了让四哥儿袭爵的心思,估摸是想着凤姐儿与王夫人相斗,就算再厌嫌凤姐儿,凤姐儿赢了,这家业也须得留在大房。
二人又是婆媳,邢夫人名分上压了凤姐儿一头,这才帮了凤姐儿一回。
眼看篆儿瘪着嘴兀自不服气,陈斯远赶忙摆摆手,将其打发了出去。红玉等也是识趣的,扯了篆儿出去,笑着将门关了。
待内中只余二人,陈斯远便蹙眉道:“怎么又帮她?”
邢岫烟笑着道:“左右都是最后一回,往后她是死是活,我是管不得了。”
有心数落邢岫烟烂好心,可对上那一对儿星眸,到嘴边的话又说不出口。这枕边人良善些,总比那冷心冷肺,处处算计的要强。
陈斯远便让邢岫烟稍待,起身进得卧房里,须臾又提了个荷包来。
邢岫烟赶忙道:“我如今也不用银钱,你又何必给我?”
陈斯远却不管旁的,扯了邢岫烟的手强塞过去,说道:“嫁汉嫁汉、穿衣吃饭,表姐早晚要许了我,如今又何必这般外道?”
邢岫烟攥着那荷包心下熨帖,却也有些别扭道:“我不是因着这些黄白之物……”
“知道知道,都是我硬塞给你的。”他笑吟吟转而道:“是了,她这回怎么问你来借银钱?她理应不缺才对。”
邢岫烟叹息一声,便将这几日妙玉情形说了出来。
陈斯远听得愕然不已,这妙玉有够倒霉的,这才几天啊?先被老尼哄去了三千两银子不说,转头儿又被贼人偷了个精光。
这也就罢了,请了官差来又被勒去二十两银子,随即又有个劳什子卢员外拿了地契撵人。
妙玉与其理论,谁知卢员外心生淫邪,说话不干不净的,竟要来拉扯妙玉。妙玉气恼之下,顿时抓了那卢员外满脸花。
邢岫烟说到此节,也禁不住哭笑不得道:“清梵眼看要打起来,紧忙往外就跑,亏得官差不曾走远,这才镇住场面。可谁料,庵中几个姑子自觉留不下,趁乱竟将她的财货尽数卷了去。一应人等身无长物,清梵只得瞒了她来寻我。”
真真儿是曲折离奇啊。
陈斯远暗忖,也唯有妙玉这等自诩不食人间烟火的,甫一离了贾家才会如此凄凉吧?
啧,却不知那贼人是不是王夫人的手尾。
陈斯远越琢磨越心痒,心下生怕被旁人摘了桃子,便拿定心思,明儿个便打发护院看顾着。
邢岫烟见其神色恍惚,只当其厌嫌了妙玉,便道:“只这一回,往后她来寻我,我也没了法子,更不会拖累你……”
陈斯远紧忙回过神来,扯了邢岫烟的手道:“一家人不说两家话,表姐又不好抛头露面,往后这等事儿只管推在我身上就是了。”
邢岫烟心下略略古怪,盯着陈斯远道:“你……莫不是又生出旁的心思了?”
陈斯远一怔,赶忙辩解道:“我?表姐还不知,我素来不待见那人。若不是表姐拦着,我都想好生落了她的脸面来给表姐出气了。”
邢岫烟顿时掩口而笑:“我与她……说不清,你甭管就是了。”
陈斯远笑着应下,心下暗自舒了口气,暗道还好遮掩了过去。
却不知邢岫烟冰雪聪明,已隐隐猜到了几分。只是她又不是正室,又哪里会拦着这等事儿?再说她于妙玉危难之际帮衬了其几回,早已全了早年教导之情,往后如何再不好多管。
邢岫烟坐了半晌方才告辞而去,陈斯远送过邢岫烟,心下生怕那妙玉被人摘了桃子,当下到得前头寻了小厮庆愈好一番吩咐。
庆愈为陈斯远心腹,哪里不知陈斯远这是犯了‘寡人之疾’?面上唯唯应下,心下自是腹诽不已。这自家大爷什么都好,就是见了嫽俏姑娘便忍不住要招惹。
当下紧忙去了一趟陈家新宅,寻了两个护院仔细交代了一番。这二人本是尤三姐重金聘请,陈斯远不过是颇有才名的举人,也是赶巧上回才挨了一袖箭,再如何京师也是首善之地,晴天白日的哪里有那么多凶徒?
因是这二人闲散了好些时日,生怕过几个月便被解聘,正愁不知如何一展身手呢。他们心下尚且不知陈斯远目的,只摩拳擦掌、跃跃欲试。
却说陈斯远一路回转清堂茅舍,心下思量着下晌时往梅翰林家中走一趟,总要听听那父子二人如何说。
正待寻几篇拿不准的文章请教一番,谁知这会子便有人来了。
“大爷,琴姑娘来了!”
琴姑娘?薛宝琴?陈斯远纳罕不已,紧忙打书房出来迎人。到得门前,便见薛宝琴领了个小丫鬟笑吟吟行来。
小姑娘一袭水红花卉纹样缎面对襟褙子,内衬象牙白立领中衣,下着象牙白长裙。头簪金钗,鬓贴粉白宫花,一双水杏眼顾盼生姿,率真明朗之余,又有一股子书卷气,瞧着竟不比宝姐姐、林妹妹稍逊颜色。
陈斯远略略恍惚间,那薛宝琴已然到得近前,敛衽一福,轻开檀口唤道:“远大哥。”
陈斯远拱手还礼,笑着道:“琴妹妹。”
宝琴起身笑着道:“这两日时常听闻远大哥人品才俊都是一等一的,可惜上回起社只略略说了几句话儿。”说话间从丫鬟小螺手里接过锦盒奉上,道:“早前便要拜会的,奈何箱笼直到今儿个方才拾掇出来。也不知远大哥喜欢什么,我便选了一盒子湖笔。”
陈斯远赶忙往里头让,道:“琴妹妹快请。论年岁我为长,合该我给琴妹妹接风才对,不想此番竟愧受了。”
宝琴立时候笑道:“远大哥这般说就太过客套了。”
二人分宾主落座,五儿立时奉上香茗来。略略说过江南风物,沿途情形,宝琴忽而欲言又止起来。
陈斯远观量神色,说道:“琴妹妹好似有话要说?”
宝琴四下瞧瞧,说道:“初次打交道,有些话实在不知如何开口……还请远大哥屏退左右。”
陈斯远心下愈发纳罕,当下打发了红玉、五儿等退下,待内中只余二人,宝琴便道:“听三姐姐说,远大哥与梅翰林有往来?”
“正是。”陈斯远应承了一句,心下暗忖,莫不是宝琴也要托自个儿扫听梅家如何说法儿?
谁知宝琴略略咬了下唇,竟说道:“先前听伯母说,梅家早已有心悔婚,却不知是真是假。”
这等话儿不好回,陈斯远便笑道:“那琴妹妹以为是真是假?”
宝琴不假思索道:“父亲在世时不过资助了梅翰林一回,婚约之事……也不过是一时戏言。”
陈斯远心下讶然,笑着道:“你兄长只怕不是这般想的。”
宝琴道:“母亲与兄长自是别有打算……可我以为,两家本就门不当、户不对,勉强凑在一处,只怕来日也是龃龉不断。如此,莫不是将这婚约作罢了呢。”
陈斯远观量着宝琴,见其面上坦然,心下禁不住好一番赞许。
薛家二房仓促来京,一则为分家产,二则也是要借了梅翰林的势谋图皇商差事。
梅翰林为清流,不拘当日是不是戏言,为名声计,若薛家二房咬死了此事,只怕心下再不爽利也要捏着鼻子认下。过后宝琴嫁过去,那梅冲本就瞧不上薛家二房,婚后又岂会善待宝琴?
陈斯远立时知道,宝琴与宝钗不同,小姑娘断不会为了薛家二房而搭上自个儿一辈子的幸福。
他不禁笑着道:“这些话儿你可曾与你兄长说过了?”
上一篇:大明:伴读万历,我爹张居正!
下一篇:返回列表